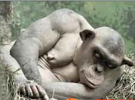□田悦芳(河北经贸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巴金是一位非常重视与读者进行文学交流的作家。从巴金小说由“作者—文本—读者”所构成的交流情境中,我们可见,作者与读者的中介是小说文本,作者与读者的关系对小说形式的生成也是至关重要的。
巴金对读者的态度是平等的、热情的,他充满了交流的渴望,也非常重视以文学来感染读者、影响读者,希望读者能够在阅读中产生文学共鸣,于是文本形式的创造也别具匠心,开放性大大增强。
一般来说,不同作家有着不同的创作动机,文学个性也就大异其趣。巴金追求文学与生活的一致,他希望读者通过文学了解自己对人与世界的看法,他的文学作品不是只供少数人享受的奢侈品,而是属于全体读者的。“我的文章是写给多数人读的。我永远说着我自己想说的话,我永远尽我的在暗夜里呼号的人的职责。”他还希望用文学为读者送上温暖与力量。“我的灵魂里充满了黑暗。然而我不愿意拿这黑暗去伤害别人的心。我更不敢拿这黑暗去玷污将来的希望。而且当一个青年怀着一颗受伤的心求助于我的时候,我纵不是医生,我也得给他一点安慰和希望,或者伴他去找一位名医。”
“把心交给读者”,是他一生都在坚持与读者密切互动的写照。带着这样一种创作动机来进行文学创作,交流成为他小说观念的重心。
为了达到良好的交流效果,一方面巴金小说文本在叙事中常常进行不同文类的杂糅。例如他常常将书信、日记等插入到小说文本中,这样一来,书信、日记等比较注重心理展示、情感渲染和细节描摹的特点在小说文本中被凸显出来,叙事视角也就此转换成了第一人称“我”,于是读者与文本以及人物之间的距离大大拉近,叙事者与作家、读者之间的对话和沟通成为现实,这种方式往往更能增强与读者的交流效果。例如《雨》中熊智君与吴仁民恋爱故事的结局就是以熊智君的一封告别信来完成的;《雾》中是以周如水读到父母的家信来收束全篇的;《秋》的尾声是以觉新写给觉慧的信来交代故事结局的。这种采用书信来为小说结尾的文本形式,读后会令读者对故事深深回味,提高了读者与文本的交流效果。
另一方面,读者的阅读期待也会直接影响到巴金对小说结构和情节的安排。例如《激流》在上海《时报》初载时并没有引起读者的关注,巴金注意到这种阅读反应后,就大幅度地改变了对小说情节进展和人物冲突的设置,后来,单行本《家》的阅读效果极大增强。又如,巴金创作《春》的过程中,就已经与一些普通读者谈论《春》的故事情节,小说结尾对淑英终于挣脱牢笼的命运安排,很可能就是受到读者阅读期待的影响。再如小说《秋》序中写道:“正是友情使我洗去这本小说的阴郁的颜色。是那些朋友的面影使我隐约听见快乐的笑声……没有他们,我的《秋》不会有这样的结尾,我不会让觉新继续活下去,也不会让觉民和琴订婚、结婚。(我本来给《秋》预定了一个灰色的结局,想用觉新的自杀和觉民的被捕做收场)。”可见,巴金对《秋》结尾的设置是与读者们的阅读期待密切相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