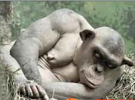□徐鹏绪(青岛大学文学院教授)
1927年至1928年,巴金曾赴法国留学。法国是当时欧洲各种人文社会思潮和艺术流派的荟萃之地,现代派艺术方兴未艾。但巴金在那里却并未像李金发等人那样,接受印象派和象征主义的影响,而是自他从事文学创作之始,便选择了求真求实的道路和方法,直到晚年的《随想录》等一系列著作,都仍坚持这一写作方向。
巴金表示,自己从卢梭、雨果、左拉、罗曼·罗兰那里学到的是“把写作和生活融合在一起,把作家和人融合在一起”。他说:“我的作品整个儿就是个人对生活的感受,我有苦闷不能发散,有热情无法倾吐,就借文字来表达。”因此,他不止一次地强调“文学的最高境界是无技巧”,文学“不是玩弄什么花样,靠什么外加的技巧来吸引人”。
针对改革开放以来,文学界远离社会生活和作家内心,故弄玄虚,盲目搬用现代主义技巧的不良倾向,巴金批评道:“现在有人把技巧强调到不适当的程度,我不这样看。我写小说就是要让读者了解作者的意思,要打动读者的心,不让人家知道怎么行?让人看不懂,就达不到文学艺术的目的了。”对于西方现代派艺术,他也从不盲目崇拜。他坦白地承认,他看不懂有些现代派的艺术品和文学作品。当有人告诉他,这些作品需要读者自己动脑筋去想时,他说:“我看来看去,想来想去,始终毫无所得。”他甚至说,可能是自己修养不够,文化水平低,知识缺乏,理解力差,所以一直想不出来。但是巴金并不为这些感到苦恼,他苦苦思索的是这样一些问题:文学艺术的作用、目的究竟是什么?难道是在沙滩上建造象牙的楼台、用美丽的辞藻装饰自己?难道我们有权用个人的才智和艺术的技巧玩弄读者、让读者猜谜?难道我们在纸上写字只是为了表现自己?文学艺术究竟是不是只供少数人享受的娱乐品、消遣品或者“益智图”?
创新是文学艺术永葆青春的前提,但不动脑子、不费气力地生搬硬套,即使套用模仿的是新出现的,是国外的,也还不是创新。玩弄技巧,故作艰深,盲目模仿,这些都是创作界和学术界的一种幼稚病、婴儿瘫。巴金的创作道路与他的文学主张或文学信念,对于矫正文风与学风,对于帮助人们认清文学界那些怪现象,的确有极大的参照价值。
除了巨大的文学成就,巴金自青年时代起,便以自己的善良、诚恳、坦荡、热情、富于正义感,赢得了人们的信任,在文艺界结交了许多朋友。无论对方处于顺境还是逆境,他都能待人以宽厚热诚,使所有与之交往的人都感受到他深厚友谊的滋润。他识曹禺于无名之时,在自己所编的刊物上发表了《雷雨》。作家萧乾身处逆境、被众人冷落时,是他伸出了热情温暖的手,萧乾后来著文称他为“挚友、益友和畏友”。鲁迅与他进行工作往来不久,就称与他“虽然还不能称为至交,但已可以说是朋友”,认为“巴金是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郭沫若赞扬他是“我们文坛上有数的有良心的作家”,是“有功于文化的一位先觉者”。茅盾在参与选编《草鞋脚》时,在他执笔的关于巴金的简介中,也赞扬其是青年学生“爱读的作家”。
巴金的作品不仅在国内被一版再版地大量印行,长期在读者中产生广泛影响,而且还被译成俄、英、德、意、日等十几个国家的文字。他的作品和为人,都受到读者和与之交往的作家、友人的普遍赞誉。